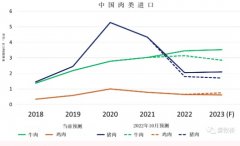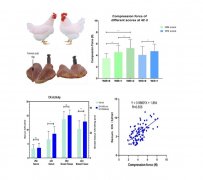在所有亲历了救治全程的人当中,患者江卓群本人是最不了解情况的一个。在长达52天的治疗过程中,这位深圳的货车司机大部分时候被注射了镇静剂,是在无知无觉中度过的。8月2日,他从深圳市东湖医院病愈出院,当各地记者们不断追问他这些天的经历时,他常常表示“回答不上来”。他只知道,经过这场病之后自己有了一些改变,而且都是些很小的
事情:不再吃鸡,也不再听以往很喜欢听的《茉莉花》。
在家里,有好几次他轻声嘟哝着:“有点儿烦。”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运气好,死里逃生了。
江卓群活了下来,差不多完全要归因于受到了堪称顶级的医疗待遇。在他就医期间,仅仅使用的各种药物就价值70万元以上,全部由政府埋单。“治疗这个病人,我的感觉就像打仗。”深圳市东湖医院院长周伯平博士说。
“从组织协调,到病情观察,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级别。”周伯平说。
“我死给你看”
科学家们很难断定病毒为何偏偏袭击了江卓群。深圳市卫生系统认定的原因是,发病前8天他吃了鸡肉。可江卓群自己却对本报记者坚持说,家里最后一次吃鸡至少也要在自己发病前两个月,当时妻子去菜市场买鸡,当场宰杀后拿回家煲了汤。另外,他自称,自己向来不喜欢吃鸡。
他很疑惑:“当时只喝了一点汤,又过了那么久,怎么会是鸡传染的?”周伯平院长对此的解释是:“他得病而家人没得,可能与病人自身的免疫能力较弱有关,他是货车司机,经常开夜车,身体比较疲劳。”
发烧是在6月3日悄然开始的,而且在最初几天里势头平缓。在江卓群租住的深圳市横岗社区安良7村的一家小医院里,医生只是给他打了治疗感冒的普通吊针。此时正是人禽流感早期治疗的最佳时机。不过,没有谁能责怪这家小医院,因为当时的深圳市并无观察到爆发禽流感的疫情。
事后香港大学的检测结果表明,此次致病的H5N1型人禽流感病毒就来自深圳本地。这或许就是禽流感病毒的神秘之所在。
“感冒”了4天之后,病毒终于图穷匕现,江卓群越烧越厉害,体温最高达到39.9度,并开始畏寒、咳嗽。由于家境窘迫,他仍然不愿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6月8日起他咳嗽加重,胸闷气促,全身各处都觉痛苦。到10日,终于不堪忍受,才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就医,并于当晚入住呼吸内科病房,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因“呼吸衰竭”转入ICU病房。
自始至终,江卓群对自己生命的关心都没有超越对医疗费用的担忧,原因是他全靠每个月2000元左右的收入来养活妻子和3个孩子,又没有上医疗保险。当天,他的妻子林静婵向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当晚交了1万元住院押金。令他们一筹莫展的是,这笔“数目很大”的钱在两天内就花完了。
就在入住这家医院的最初阶段,江卓群的病情陡转紧急。
O伦第2版v 10日当夜,江卓群高烧达40度,呼吸困难,不停地咳嗽,“吐了一夜的血”——吐出的“痰”完全是红色的,呈血液特有的泡沫状,用来接“痰”的手纸几乎装满了整整一个垃圾桶。实在难以忍受痛苦的他最后对护士说:“我死给你看!”于是使劲儿用头撞墙,撞了5下,“太痛了,撞不死。”就这样他熬了一夜,“好辛苦”,到天亮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X光片证实,这晚之前他的肺部阴影还只是在左肺局部,而这晚之后就已经弥漫到左右全部肺叶。
到次日被深圳疾控中心认定为疑似H5N1型人禽流感患者时,江卓群已经到了发病的第9天。
这就是他成为“全国治愈的人禽流感患者中患病最重的一位”的全过程。据深圳市东湖医院医生事后撰述的《临床分析》记录,转入东湖医院时的江卓群多个脏器严重损伤,“免疫能力低于艾滋病晚期病人”,气若游丝而有“危重病容”。
别无选择
6月12日凌晨2点半,江卓群被转入深圳市东湖医院的隔离ICU病房。仍然用借来的钱,林静婵交了1.5万元住院押金——不过在广东省和国家防疫中心确诊江卓群为人禽流感患者后,这笔钱被确定可以退还。
这天凌晨1点,东湖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周亚红正在江西的一座名山里,参加医院的活动。她接到了周伯平的电话,“转来一个病人,很可能是禽流感”,要求她和同事马上赶回医院。
同样的电话也打给了感染病区主任刘水腾。一个小时后,刘水腾就已经转移了12个病房的病人,腾空了一层楼。
直到几天之后,林静婵才被允许在感染病区二楼的抢救室窗外观望一下病床上的丈夫。她没什么文化,不懂得如何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很多天后,记者们问到首次看到昏睡的丈夫时她在想些什么,回答出乎人们的意料:什么也没想。最终,这个回答被曲解为“大脑一片空白”。
在丈夫转院之后,她乐观地意识到,这一回可能有救了。她早就在电视上看过,禽流感这个病跟别的病不一样,很可能会死人。但是,“医生对我讲,政府说了,付出一切代价抢救病人。”
林静婵从此坚信,丈夫肯定会康复,因为她“相信政府”。与她相比,周伯平院长倒要悲观得多。
“这个病人刚入院时,经初步检查之后我就很不乐观,当时我想,治好的话就是一个奇迹。”周伯平说。不过他很清楚,而对如此危重的病人,这一次他和他的医院没有别的选择:全力救治。
迄今为此,广东省一共出现了两名人禽流感患者,一位姓劳的广州病人已于此前去世。而“国际上的人禽流感死亡率是50%多,国内是60%多。”刘水腾说。
周伯平则认为:“人禽流感病例一旦出现就会引发全球关注,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深圳靠近香港,活禽供应停止一天,就要损失几十万。这个病人治不好,有人就会认为是卫生体系不好,投资环境不好,还会影响社会安定。”
深圳市卫生局长江捍平很快到了医院,转达了多位省市领导的批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患者。
这简直就是生死时速!东湖医院紧急指派了由6名医生组成的临床治疗小组,另由市卫生局协调,从外医院派来了15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护理的护士则先后达到20多名。同时,专家组也开始运作。深圳市参加此次救治工作的专家共有8名,包括了全市传染、呼吸、ICU、放射、微生物和药理等专家。此外,卫生部的2名专家、广东省卫生厅的8名专家也参加过救治工作。
若非如此,你很难相信这样一位病人还活得成:肺、心脏、肾、肝、血液系统和免疫系统,全部处于崩溃的边缘。江卓群的妻子林静婵事后描述说,“肺都烂了。”在6月16日,为了长期使用呼吸机,这家医院给江卓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其后的几天中,每次为其吸痰时抽出来的都是血,“一管一管地抽出来。”
一般人很难了解,一种呼吸系统的病毒会侵害心肌细胞,使江卓群的心肌细胞中广泛出现水肿和空泡,即明显的中毒性心肌炎症状。正常人的CD4+T免疫细胞为600个/UL,而他当时绝对计数最少只有5个/UL。
东湖医院的医生猜测,禽流感病毒可能直接攻击了免疫细胞CD4+T。病毒之害如此剧烈,让袁静医生做出了这样的类比:SARS还只是摧毁免疫系统的一半,人禽流感则是完全摧毁。
2003年,东湖医院曾是深圳市收治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当时上报了确诊病例10多例。
即便如此艰难,深圳市卫生系统除了倾尽全力外别无选择。医疗小组每半小时记录一次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并随时调整,至7月5日止,积累了厚厚的一大叠打印纸。周亚红带领护士小组,每半小时记录一次他的体温、心律、血糖和生命体征,每半小时为他拍一次背、吸一次痰。每半小时,三名护士配合,为病人翻一次身,小心翼翼地不弄乱他身体上的至少6条、至多9条医疗管道。
ICU病房的特别护理标准是,在每个班时中,护士和病人“一对一”——“其实是做不到的。”袁静说——而这一次不仅做到了,而且达到了一对三。另外,如有需要,忙于其他工作的护士可以随时抽调过来。
每隔两小时,就会有两名护士为这名货车司机按摩一次。她们不停地给他擦身、全身涂油、护理嘴唇、点眼药水。最初她们都预防性地吃了抗病毒药物“达菲”,恶心干呕,仍然不停地工作。
“我们压力很大,生怕出半点儿纰漏。”周亚红说。